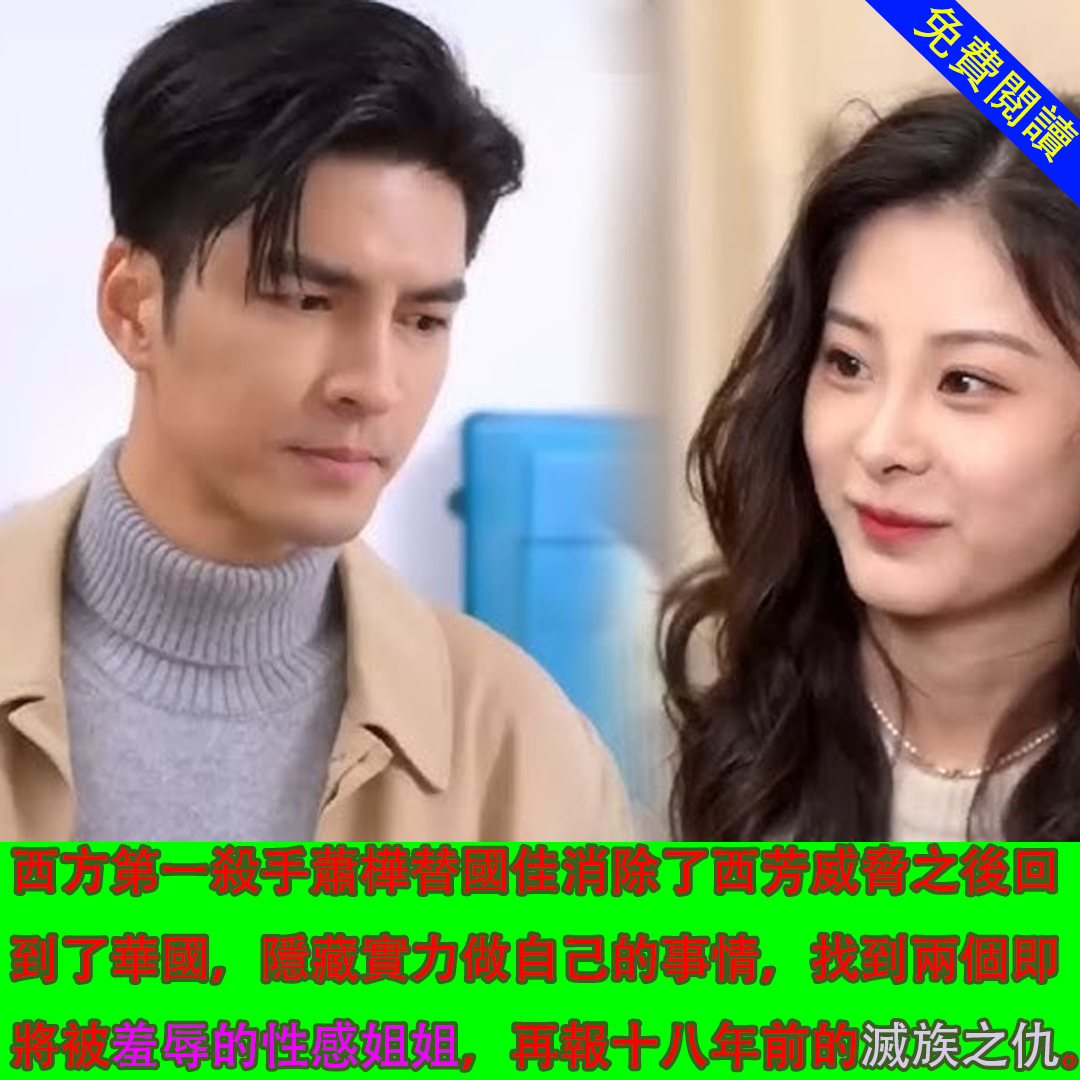宇文隆完全沒有招架之力,被宇文佑雨點似的拳頭打得隻管抱着頭往角落裡縮,看上去狼狽又可憐。
然而宇文白也好,太皇太後也好,闵太後也好,全都隻管看熱鬧不管事。
蕭太嫔尖叫起來:“幹什麼?幹什麼?當着陛下和太後娘娘的面就敢這樣沒有王法?”
康甯公主更是不顧一切地從座位上站起來,沖過去拉宇文佑,又叫其他人去幫她哥哥:“你們都是傻的麼?怎麼就看得過去?”
宇文初垂了眼,一言不發。
太皇太後這才闆着臉重重一砸杯子,怒道:“住手!”
宇文佑狠狠一腳踢在宇文隆的腰上,再一口唾沫吐到他臉上,才停下來,一言不發地垂着眼站直了身子聽訓。宇文隆敢怒不敢言,憋氣地将袖子擦了臉一把,撲到太皇太後跟前哭訴:“母後要為孩兒做主啊!”
“荒唐!堂堂郡王竟然在冬至家宴上大打出手!你們從小學的規矩禮儀呢?看看你們這模樣……”太皇太後的手指從宇文佑和宇文隆身上挨個兒點過去,一臉的恨鐵不成鋼,“真是丢了宇文家的臉面!将來到了地下,我簡直無顔面見先帝!”
宇文白稚嫩的聲音響起來:“皇祖母息怒,别為了這種小事兒氣壞了自個兒的身子骨。家宴嘛,自然不能和平時相比,兩兄弟喝多了酒鬧點小矛盾不算什麼,打打鬧鬧的也就過去了。”
闵太後也笑:“還從未見過老九如此生氣呢,說來聽聽,老八怎麼招惹你了?”
宇文佑看了明珠一眼,垂下眼咬緊牙關一言不發。
明珠被他這一眼看得莫名其妙的,但她怎麼也想不到起因居然是宇文隆在背後侮辱亂說了她。
宇文白見宇文佑不肯說,笑了笑,再去問宇文隆:“八皇叔,你來說。”
就算是借給宇文隆十個膽子他也不敢說出真相,不然太皇太後也好,宇文初也好,都容不得他,傅明珠隻怕當場就敢往他身上扣菜盤子。他隻能自認倒黴,别别扭扭地道:“是我不好,不該和九弟亂開玩笑。”
“雖然是親兄弟,開玩笑也要有個度。雖是家宴,然而身份不同,規矩更不能亂。當着國君的面就敢如此放肆,到了外頭還了得。過節,我不想多為難你二人,都到外面去跪着吧。”太皇太後一錘定音,勢必要重重打壓這些越來越不聽話的庶子,叫他們好好收心乖乖聽話。
蕭太嫔急了,忍不住就想為宇文隆求情,然而剛開了個口,就看見宇文白眼神陰冷地看着她笑:“太嫔有話要說?”
蕭太嫔看到宇文白的表情,下意識地一陣膽寒,裝成義憤填膺的模樣大聲道:“就該狠狠的罰!這麼大個人了還不知道輕重,别輕饒了他!給他教訓,看他下次還敢不敢!”
衆人都看出了蕭太嫔的裝模作樣,但一般人通常都是笑笑就算了,偏宇文白不是一般人,他十分感興趣地征求起了蕭太嫔的意見:“太嫔真是深明大義。那麼依您所見,該怎麼罰才能讓八皇叔長記性呢?”
蕭太嫔一下子就給問住了,她深知這熊孩子的刻薄殘忍之處,想往重裡說吧,深怕他來句“就依你所言,八皇叔照辦吧!”往輕裡說吧,他肯定會連着她一起辱罵,還不知道有多丢臉呢。
宇文隆見他親娘被為難住了,連忙大聲道:“陛下,臣錯了,您怎麼罰臣都心甘情願。”
宇文白摸着下巴想了一會兒,哈哈一笑:“朕今日祭天大典,着了一雙新靴子,不甚合腳,這會兒腳還酸着呢。這樣吧,八皇叔,罰你給朕脫靴揉腳。”
天子是九五至尊,别說給他脫靴揉腳,就算是給他擦屁股也該得。但宇文隆不是别人,他是先帝之子,天子的皇叔,堂堂郡王,并不是奴婢,在這樣的情況下,宇文白當着衆宗室的面提出這樣的要求,無疑于折辱。
這是給之前蕭氏依附太皇太後并試圖求娶明珠而得到的報複。
宇文隆跪伏在地上,額頭上的青筋都暴了起來。他有雄才大志,也想一飛沖天,若是給小兒皇帝當衆脫靴揉腳,将來就算是登上至尊寶位,也是一輩子揮之不去的污點。叫他怎麼甘心?
宇文白笑聲寒涼:“怎麼,八皇叔不樂意?是不是心裡看不上朕這個天子,覺得朕不配啊?”
這話逼得死人。
宇文隆咬着牙行了個禮,道:“臣遵旨。”
宇文白看向宇文佑,宇文佑緊張得直咽口水,就生怕宇文白把他喊過去和宇文隆一起瓜分了左右兩隻腳。然而宇文白隻是一笑:“九皇叔是性情中人,下次記得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這次就算了,朕饒了你了,下去坐着吧。”公然是完全無視了太皇太後之前的旨意。
宇文佑默然行了一禮,飛快地退下去了。
宇文隆跪坐到宇文白面前,顫抖着伸手抱住宇文白的腳,要哭似地替他脫了靴子,再把他的腳放在自己的腿上揉了起來。
宇文白愉快地欣賞着他的表情,轉過頭和太皇太後說道:“雖然在家宴上當衆脫靴揉腳不太好,不過朕想,朕富有天下,乃是九五至尊,這麼點小事兒也不算什麼吧?何況這麼冷的天,與其讓兩位皇叔去風口裡跪着,還不如我們叔侄倆增進一下感情,皇祖母您以為呢?”
分明就是和太皇太後叫闆,在人前打壓太皇太後的威信,卻被他說得輕描淡寫、孩子氣十足的。太皇太後眯了眯眼睛,輕輕一笑,說道:“陛下雖是好心,然則禮法不可輕廢。長幼尊卑還是要講的,你這樣對待自己的叔父,是不敬。”
“哦?”宇文白換了一隻腳,示意宇文隆:“揉揉小拇指那兒,那裡最疼。”再回頭和太皇太後繼續說道:“道理是這樣,但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何況朕隻是讓他揉揉腳呢。”又問宇文隆:“八皇叔,你覺得委屈嗎?”

![拯救全息遊戲中的他[無限流]](/uploads/novel/20240510/97dde85b6b3bd61c5798242efbfdd63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