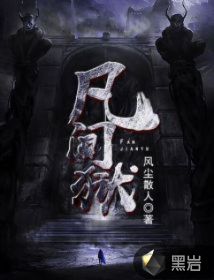沈念禾開始慢慢理解到了什麼是裴繼安眼中的“客”字。
這“客”實在“客”得很徹底。
他雖然依舊體貼照應,樣樣都想着自己,看起來好似同從前沒甚差别,可那細微處的做法,卻是讓人如鲠在喉,難受極了。
飯畢,裴繼安收拾碗筷,也不說什麼,徑直回了廚房,剩得鄭氏在一旁,欲言又止地看了沈念禾一眼,見她眼睛跟着裴繼安往廚房走,手裡拿着插着半片林檎果的竹簽,半晌不記得去吃,便猜到這兩人之間有了什麼事。
鄭氏本是過來人,深知此時自己不要多摻和最好,也不去問,手裡本來還削着凍橙,卻是忽然“哎呀”了一聲,道:“一時忘了,我同人訂了時鮮果子,得趕緊出去拿一趟。”
又忙把削了個頭的橙子遞給沈念禾,道:“你三哥愛吃橙子,我這一處趕着沒空,你幫着收一收尾。”
語畢,将刀往桌上一放,拔腿就朝外走。
沈念禾倒也沒有多想,拿了刀起來,心不在焉地給橙子削皮,因她手笨,偏那橙子皮又薄,等到回過神來,低頭一看,手中橙子早被她削得同狗啃一般坑坑窪窪的,實在不好意思擺出去,隻好放在一邊,另又取了一個過來。
她在此處同個橙子較了半天勁,裡頭裴繼安早已收拾好了,才出得廚房,見沈念禾手中持刀,動作間頗有些笨拙,便連聲音都不敢大出,隻站在門口,等她把那刀放下了,複才走了進來,道:“你不慣做這個,放着就是。”
沈念禾見得裴繼安,本想讓他吃果子,隻是看那橙子汁水淋漓的,哪裡有臉拿出來,隻好把手縮得回去,沒話找話道:“嬸娘說訂了時鮮果子,已是到了時辰,方才出去拿了。”
裴繼安點了點頭,也不說話,卻是拖過一張交椅在邊上坐了,取了桌上的小刀,另取了一個凍橙削皮。
他的手極巧,運刀如飛,仿佛隻是眨眼的功夫,就把那橙皮削成不中斷的長條,外黃内白,螺旋一般,一圈圈又湊成了一個空橙子。
沈念禾就坐在邊上看着他把橙子皮削掉,将肉切成整整齊齊的八瓣,又用小竹簽分别插了,取個碟子擺了個盤,重新推到她面前。
“吃罷。”裴繼安語氣淡淡的。
沈念禾更難受了。
此時此刻,便是龍膽鳳肝她都吃不出什麼味道來,哪裡還有心思嘗什麼橙子,猶豫了一下,還是坐直了身子,道:“三哥,今次是我做得不對,隻當時實在沒有想太多——我近日雖是覺得仿佛有人在暗中窺視,畢竟沒有證據,也不曾捉到人,早間見得那一個,因是在公廳之中,左近都是自己人,想着他如若身有歹心,不可能逃得掉,況且三哥這一處又太忙,我不願拿這等小事來……”
她話未說完,裴繼安就輕聲反問道:“你又安知這于我是件小事?”
沈念禾聽得微愣。
她平常心髒是“撲通撲通”的跳,此時卻是隻有“撲”,“通”的一聲仿佛被吞掉了似的。
等跳過了那一下,沈念禾一下子就清醒過來,隻覺得手心微微發汗,心也跳得越發快了起來。
她心中生出一種預感,那感覺似乎是惶恐,又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緊張,隻好看着裴繼安,本想要說些什麼,忽然見得對面的人把椅子往前挪了挪,與自己幾乎隻錯隔而坐。
裴繼安往前坐了坐,距離沈念禾隻兩步遠,雖不至于逾越,然則比起平時,又多了些親近。
他問道:“你想同我做自己人,還是外人?”
什麼是自己人,什麼又是外人?
沈念禾想問又不敢問,隻腦子裡有一道聲音告訴她,如果問了,之後一定會後悔,可另又有一道聲音同她說,如果不問,會更後悔。
她手心發粘,耳朵發熱,就呼吸都變得局促起來,嗓子裡頭發幹。
裴繼安問完這一句話,卻是一動不動看着她,等她回答。
他眼神專注,神情十分認真,似乎今次不等到一個确切的答案便不肯罷休一般。
沈念禾抓着交椅的把手,勉強笑問道:“三哥又把我當什麼人呢?”
把這問題又推了回去。
裴繼安做事從來沒有退縮過,今次既然已經開了口,便絕不會隻說一半,吊着事情在半道上。
他将手輕輕搭在沈念禾側面的桌子上,仿佛半臂虛環着她一般,整個人往前傾,隻把自己的上半身放得同她一般高,平視着道:“你才來時,就在隔壁廚間我問過一句話,還記不記得當時你是怎麼回的?”
沈念禾一下子就記了起來。
隻她還沒來得及做反應,裴繼安已是又道:“當時你初來乍到,許多事情并不甚清楚,眼下已是在宣縣住了半載,諸事皆熟,再不複從前,我隻想再問你一回——你覺得我為人如何?”
沈念禾喉嚨幹澀,欲要回話,那話卻被卡住了。
裴繼安面上并無半點笑意,當中隻有鄭重其事,把當日那後半句話再一次補齊,問道:“念禾,你看我為人如何,可堪托付終身?”
沈念禾腦子裡頭亂糟糟的,隻覺得這一句問話乃是意料之中,卻又出乎意料,張嘴要說話,又不知要說什麼。
裴繼安道:“我而今雖然隻是個小吏,隻有陋室三兩間,雖有三分薄财,卻半點比不上從前的沈官人,平日裡忙于雜務不說,還要你來相助,可我為人踏實,人品端方,最要緊是一心一意,但凡有一點可能,便不會叫你吃半點苦……”
他的話同數月前相比,内容上并無什麼出入,然則此時無論表情還是眼神,俱是變了一個人一般,原本的認真與誠懇并未改變,卻又多了一種熱切的情緒在其中。
沈念禾被他看得整個人都仿佛被架在火上烤一般,渾身發熱,有一瞬間,腦子幾乎不會轉了,張口就要答應,然則那一個“好”字尚未說出口,忽聽得前院敲門聲,一人在外頭大聲叫了兩句,先喊嬸娘,又喊三哥——卻是晚歸的謝處耘。
沈念禾登時打了個激靈,一下子清醒過來,連忙坐直身體,提醒道:“三哥,謝二哥回來了!”
裴繼安慢慢把手收了回來,又看了她一眼,複才站起身來,往外去開門。
沈念禾尋得這個機會,哪裡還敢停留,連忙轉身就回得房中,把門掩了。
她坐在桌前,隻覺得雙頰熱乎乎的,仿佛發燒了一般,攬鏡自照,果然滿臉暈紅,眼眸好似含着秋水,而心髒更是過了這許久,仍在狂跳,半晌不肯慢下來。
裴三哥可堪托付終身?
自然是可的。
可他們兩個,當真合适嗎?
沈念禾手中抓着銅鏡的邊框,腦子裡頭全是半年來自己同那裴三哥相處的情形。
他知道她喜歡吃的東西,會給她收拾桌案、整理術算草稿,會送她出入,她想要家裡的書印得好看,他就去找書法大家,她想去京城打探消息,哪怕路上會多再多麻煩,他也一口答應下來,她略病一場,他就四處尋了滋補藥材來做藥膳……
林林種種,數不勝數,一時之間甚至不能全數記得起來。
如果說一聲不,這樣好的一個人,就要讓給别人了……
想到将來他會對别人這樣好,甚至更好,而對上自己,就會變得如同今日下午時一般,禮數周全、客氣倍至,卻又疏遠異常,沈念禾的心就難過得厲害。
喝過了好肉炖出來的濃湯,誰又願意去嘗涮鍋水呢?
沈念禾腦子裡全是方才裴繼安問的那一句話,半晌沒有辦法從裡頭出來,然則等到腦子清醒了些,卻又想起沈家同馮家的官司,又想起沈輕雲、風雲、馮蕉夫婦的事情,繼而還有裴家的事,又覺得即便出于良心,自己都不能隻圖人的好,就帶累旁人。
***
裴繼安坐在桌前,半晌沒有說話。
謝處耘卻是一面喝湯,一面喋喋不休的,道:“好險三哥還給我留了湯飯,你是不知道,我今日忙了這一通,已是餓得前胸貼後背——三哥,你走得快,沒瞧見謝郭向北的臉……啧啧,他怕是死也想不到居然還會遇得這樣一遭事……”
他一面吃一面說,眉飛色舞,興緻勃勃,隻差沒把郭向北的臉是如何變了由灰變青,又由青變紫,最後轉成豬肝色一一形容出來。
裴繼安卻隻點了點頭,示意自己聽到了,并不插話。
他方才去給謝處耘應門,回來之後就發現沈念禾早趁着這時候溜回了房,哪裡還有半點蹤影。
人在時他不覺得自己的做法有什麼,此時人一走,他就有些清醒過來,看着邊上啰啰嗦嗦說個不停的謝處耘,方才去開門的時候還想把他扔去庫房看一晚上大門,眼下倒是生出一點子慶幸來。
——太倉促了,還不到時候。
今日的事情簡直像是一件趕着一件。
謝圖偷偷潛入庫房,意圖的修改賬冊乃是他意料之中的,甚至可以說在後頭有過推波助瀾。
可這渣滓險些在裡頭遇到沈念禾,甚至有可能真正欺負她的事情,卻是他半點沒有防備到的。
幸好還有郭向北擋了這一擋。
隻是被這事情刺激了一回,等到查核清楚,又聽沈念禾說了被人窺視,卻又不告訴自己的的時候,裴繼安一下子就氣惱得不行。
遇上什麼事情都不同他說,她這是把他當什麼了?
養了這麼久,明明都養熟了,到底是哪一處出了錯,她就是不把自己當做一家人看?
裴繼安再怎麼看起來老成,畢竟不過未及弱冠,尤其于男女相處上頭,更是一竅不知,全然憑着一股子自覺行事。
他這次沖動完了,理智一回得來,就覺得自己的做法有些過分急迫,未必是個好選擇。
——這沈妹妹眼下還把自己當做兄長,匆匆吐露心聲,多半會把她吓跑。
不過也不是全然沒有好處。
不逼一逼,叫她知道自己待她的特殊之處,她就永遠也不會從那龜殼裡頭鑽出頭來看一看自己,總以為扛着老殼閉着眼睛慢慢走就是安全的。
這一回點醒了,雖然沒能得個答案,看她今日反應,不像是很抵觸的模樣。
今天話也沒能多說幾句,回來時兩人都是分頭走的,晚上她飯又吃得這樣少,還是明天早一點起來,給她弄點好吃的。
本來身體就不好,免得還把脾胃給弄傷了……
另還有民伕已經征調好了,那謝圖已是被郭保吉捉得起來,以此人從前犯下的那些事,一旦牆倒,遲早衆人推,
叫這人渣還敢亂動腦子,什麼人都敢打主意,還敢在外頭犯下那許多喪心病狂之事。
不過此刻時間已經很緊張,新人上來未必能再短時間内采買夠,自己也得幫一把手,不然那圩田怕是沒法順利建起來。
……咦,已經戌時了,那沈妹妹晚上隻喝了兩口湯,有吃了幾塊肉菜,居然抵了這樣久都還沒動靜,如若餓了怎的辦?
難道是聽得方才自己說了那一通話,又想着謝處耘一起在外頭,不好意思出來?
想到這一處,他連忙把腦子裡那等亂糟糟的念頭甩掉,本想要定一定神,卻老是想起沈念禾一個人坐在房裡,餓得胃疼的場景,一時之間,就什麼都記不起來了。
裴繼安這一處在走神,先還想着正事,後頭拐到沈念禾頭上,就越跑越偏,努力正了幾下,見正不回來,索性也懶得去強迫自己,便站得起來,去廚房裡盛了兩碗湯出來,先分了一碗給謝處耘,複才那托盤帶着另一碗要去後院。
謝處耘喝了兩大碗湯,嘴巴依舊沒被堵住,見得裴繼安要去後院,三口兩口扒完飯,就跟了過去。
裴繼安卻不知道自己後頭多了個跟班。
他端着托盤先敲了敲沈念禾的門,等得了回應,才推門而入,将那雞湯擺在桌上,道:“做不做自己人都沒關系,卻不能為着我這個外人,餓着自己肚子吧?”
語調溫柔,語氣裡還帶着幾分打趣,仿佛一瞬間,又回到了曾經那個如琢如磨的君子裴繼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