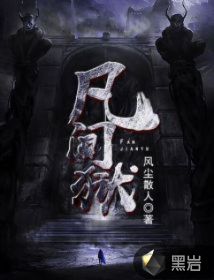瘋子!
這就是個瘋子!
!
不知道是古墓裡悶的,還是緊張,我腦門上沁出了大片的汗水,止不住的往下流。
狠人,我不是沒見過。
但這根本就是亡命狂徒!
大家下坑不外乎就是窮的過不下去了,所以才從死人碗裡搶口吃喝,為的不還是繼續把日子過下去?
哪有下坑就是為了找死的呀,這是本末倒置。
轉眼的工夫,軍哥已經走了過來,他很坦然,雙臂高舉,一手握着玉珠子,一手拿着手槍,示意自己不會開槍,卻一下子把胸口頂在了大兵槍口上,與大兵臉貼着臉,滿臉挑釁的說道:“年輕人,你日子還長,要是和我一樣真不想過了,那就開槍!
”
大兵臉上的肌肉都在抽搐。
我了解他,他性子一上來,真敢幹了軍哥。
但,軍哥說的對,我們這玩意跟散彈槍一樣,一打一片,和他手裡的家夥不一樣,沒有準頭,不可能就跟他殺胡子一樣,一槍爆頭,隻要走點火,我們就得一起死在這。
我不想死。
對峙良久,我歎了口氣,手放在了大兵的胳膊上,把他端着的槍壓了下去。
“你走吧!
”
我對軍哥說道:“這回,我認栽。
”
“該認!
”
軍哥點了點頭,臉上竟流露出一絲落寞,說道:“小九哥,你很年輕,我混這麼多年沒混明白,你卻比我明白,知道進退,你這種人能活很久。
”
說完,他開始後退,倒是不急着走了,身上揣着炸藥,就這麼在我們眼皮子底下晃蕩,簡直和挑釁沒區别。
他轉悠了兩圈,最終在小二身邊停下,一扭頭,沖我笑了,道:“其實,小九哥,這回你該謝我,我多拿點也是應該的,我不做了這倆,你們都走不掉!
”
他們内部有問題,這我看出來了,遲疑一下,問道:“怎麼說?
”
“這王八蛋,是個出了名的點子。
”
軍哥指着小二的無頭屍體,滿臉憤慨。
點子,是黑話,誤入歧途的人都知道什麼意思。
犯罪分子裡也有硬骨頭和軟骨頭,硬骨頭進去了,怎麼折騰都不開口賣同伴,軟骨頭進去了,不用打不用罵,吓唬一下全交代了。
慣犯裡頭的軟骨頭,局子裡的人一清二楚,每次要抓人,先找這些軟骨頭,給根煙,吓唬幾句,打聽點情報,這種軟骨頭,就叫點子,就跟點名似得,他們點到誰,誰倒黴。
軍哥問我:“點子被逮進去什麼下場,你知道吧?
”
我點了點頭。
坐牢的分三六九等,強奸犯和點子是最讓人瞧不起的,進了号子以後,人家叫他們尿馬,夜裡号子裡的大哥起夜,他們得過去背着人家去上廁所。
而且,誰不爽了就可以撸他……
反正,點子真進去了,沒好下場。
“我跟他是勞教的時候認識的,被打的很慘。
”
軍哥沉吟了一下,說道:“然後,我幫了他,出來以後跟我混了,結果特麼混着混着和我老婆混在一起了,他、胡子、閻王,這仨這次就合計做了我,他們自己獨吞。
要不是我事先接到了點風聲,而且閻王也意外死了的話,這會兒躺着的恐怕就是我了,你倆也得一起倒黴,我們四個先做了你倆,然後他們仨幹掉我。
”
說完,軍哥再不停留,轉身就走,扯着盜洞口垂下來的繩子,三下兩下就爬了上去,身手很好,臨到進盜洞之前,他才忽然轉頭對我說道:“小九哥,青山不改,綠水長流,這回我占了便宜,情我接了,下回再有活兒,你們拿,我不碰。
”
然後,他就這麼堂而皇之的在我們眼皮子底下離開了,但直覺告訴我,他們内部的問題絕不僅僅是這些,關于這座墓,他知道很多,而我也有預感,我還會見到他。
他走後,大兵咒罵了起來:“媽的,這回全白幹了!
”
說此一頓,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苦笑道:“咱哥倆除了剛入行那會兒,什麼時候栽過這麼大跟頭?
這回是陰溝裡翻船了,讓這幫子刁民給坑了。
”
不過,他大大咧咧,很快就想開了,一轉眼工夫喜笑顔開,朝那棺材走了去:“好在咱哥倆沒事兒,雖然再沒什麼東西了,但這把破劍也拿着吧,回去給我家妹子當個燒火棍使使,至于秦教授,小九你也甭想那麼多,回頭再看看有沒有别的線索,隻要你吱聲,我和你一塊去。
”
我歎了口氣,由得他去了,蹲在墓室一角,點了根煙兀自抽着。
大兵倒是真較真,他确實去倒騰棺材去了,裡面死人骨頭被折騰的“嘩啦啦”作響,然後他就把那把破鐵劍拎了出來。
這時,他忽然輕“咦”一聲,轉頭對着我招手:“哎,小九,你快過來瞅瞅,這棺材裡面有字兒!
!
”
“能有什麼字兒!
”
我擺了擺手:“正煩着呢,你趕緊的,拿了東西咱就走,這地兒剛剛開槍了,說不得護林員正往這邊走呢,可别被逮個正着,那兒躺着倆死人,這黑鍋咱不背!
”
“真有字兒,你快來看看!
!
”
大兵有些着急,說道:“而且這字兒好像最近才寫上去的!
!
”
大兵沒文化,但和我刨墳倒鬥多年,墓裡的東西是新鮮的還是陳年的,他能認得出來。
一時,我也奇怪了。
這地兒就一條沒打通的盜洞,也就是說除了我們沒人來過,怎麼可能會有最近才寫上去的字?
當即,我起身朝那邊走了過去。
果不其然,棺中确實有字。
那字看着像是用手指頭摳上去的,痕迹清晰,看着确實是前不久才摳的,就在墓主人的屍骨下面壓着的,故而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沒看見。
“劍,一定要帶走。
”
棺材裡就這六個字。
盯着這一行字,我渾身不可抑制的顫抖着。
很熟悉的字體。
因為,這字,就是秦教授的筆迹,他曾經教過我文化知識,上面有很多東西他都會仔細的批注,對于他的筆迹字體,我實在是再熟悉不過了,斷然不可能認錯。
他留下這句話,到底是在提醒誰呢?
這把看着就跟破銅爛鐵一樣的劍,有那麼重要?
還有,秦教授是從哪裡進來的?
現在他又在哪裡?
我從大兵手裡接過了那把生鏽的鐵劍,入手微涼,頗為沉重,遲疑片刻,我輕聲說道:“這把劍,怕是不能給你妹妹當燒火棍用了,秦教授的事兒,沒那麼簡單,咱們先走,這事兒總有明白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