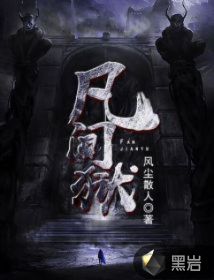趙子良眼中的憤怒是顯而易見,瞳孔中就差有小火苗噴湧出來了,隔着大老遠我都能聽到他牙齒咬得“咯吱咯吱”作響,幾乎是一字一頓的說道:“你别太過分,留下陳瑤,你們可以走。
”
走?
走是不可能走的。
任務失敗,等于死。
黎明是個殘酷的地方,尤其是對于我們這些新人來說,更是如此,不斬殺趙子良,我們回去後一定會被人道毀滅。
其實趙子良是個挺博人同情的主,可惜他遇到了我,我從來都不是個舍生取義的人,為了活下去,我什麼事兒都能幹得出來。
雖然手段是下作了點,但隻要能達到目的,我不介意髒點。
我隻能說,其情可憫,其人必誅!
趙子良是個聰明人,看我的模樣就知道什麼意思了,耐心消磨殆盡,猛然踏出一步。
我手中的九龍劍頓時向前挪動一分,陳瑤身子立刻繃的筆直,白皙的脖頸上湧出大量鮮血。
“别!
”
趙子良急了,立即退了回去。
“下不為例。
”
我看似鎮定,實則心裡暗自給自己捏了把汗,完全是本着性命險中求的心思在賭博,不動聲色的對趙子良說道:“給你三分鐘的時間,還有什麼想說的盡快。
”
趙子良面色陰晴不定,時而怒火沖天,時而又溫情脈脈,不過最終還是溫情占據了上風,他很清楚,他的速度再快也快不過我手裡的刀,須臾後,他忽然悲怆的大笑了起來。
“值麼?
到底值不值?
”
他不斷重複着這個注定不會有答案的問題,與其說是在問我們,不如說是在問他自己。
不過出乎我預料的是,趙子良竟再沒有和陳瑤說話,或許是想到了傷心處,淚水洶湧而出,模樣凄慘,擡頭靜靜看着我,說道:“好,我死,她活,希望你說到做到,我知道你們黎明有殺人滅口的習慣,對于所有看見我們這種生靈的人都會果斷殺之。
不過,我還有個要求。
”
我揚了揚眉:“說!
”
“我要他!
”
趙子良伸手指向李長帆,一字一頓說道:“我要殺的人還差一個,他必須跟我一起死!
”
“不行!
!
”
李長帆早就被眼前發生的事情給吓傻了,一下子從地上跳了起來,神情激動的喊道:“我和你們一樣是人,不是他這種怪物,而且我有錢,我可以給你們很多很多錢,你們不能害我!
”
“不好意思,任務完成是我的唯一标準,死多少人我并不關心。
”
我靜靜看着李長帆:“反正人很多,不差你這一個,剝開有錢的外衣,你覺得自己還剩下什麼?
我倒是覺得你活着反而會讓更多人受累,與蛀蟲無異,所以,隻能委屈一下你了!
”
李長帆臉色一變,不再和我多說,轉身就想逃走,不過他吃的肥頭大耳,紙醉金迷的生活早就把身子掏空了,真跑起來又如何能跑的遠?
神經病一個箭步就追上了,擋在他身前刹那,擰身一腳招呼在他胸口上,瘦弱的身軀裡爆發出千鈞力道,李長帆慘叫一聲,即刻倒飛了出去,穩穩落在趙子良腳下。
看着趙子良再次變得猙獰的臉,這個慫包吓得屎尿都出來了
這是一場屠殺。
趙子良與野獸無異,獠牙尖銳,爪牙鋒利,撲上去近乎把李長帆給活活撕碎了,最後隻留下一大灘跟餃子餡差不多的血肉模糊的東西,花花綠綠,看不出人的形狀。
直到李長帆死的不能再死,趙子良才終于罷手。
倉庫在熊熊烈焰中開始崩塌,沖天的火苗把趙子良近乎扭曲的臉照的紅彤彤的,已經看不出粘稠的血漿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他放聲狂笑着,身上激蕩着與他相貌絕不相符的豪邁。
就連我都不得不承認,這是條漢子。
至少,在他們這個族群裡,他是唯一一個沒有在沉默中死去的主。
少頃後,他起身看着我,忽然伸出了手:“借刀一用!
”
叮當!
一聲脆響,一柄短匕落在趙子良腳下。
匕首鋒刃上躍動着冷冰冰的藍色弧光。
姬子面色蒼白,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指了指匕首,輕聲道:“用這個吧,很鋒利,而且淬過毒,不會有什麼痛苦。
”
“謝了。
”
趙子良看了姬子一眼,輕輕把玩着匕首,指肚刮擦着刀刃,沉默片刻,忽然擡頭對陳瑤說道:“我早想到了這一刻,從我動手殺人起,我就知道他們這些人一定會來的,就算這次我赢了也一樣不會有什麼好日子過,他們會追殺我到天涯海角,這次是幾條小雜魚,下一次就會是高手,下下次或許是更加強大的存在,終有一天我會死,與其那樣,還不如早早了結,也放你一條生路。
”
他嘴角掀起一抹苦澀,搖了搖頭,歎息道:“你餘生多自愛。
”
餘生多自愛。
這就是他給陳瑤最後的忠告,也是他的遺言。
對怯懦者來說,有朝一日一旦打破鉗制在身上的禁锢,就會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洪荒猛獸,昔日有多少退讓和忍耐,爆發後就有多少勇氣,發起狠來不僅對别人狠,對自己更狠。
趙子良就是這樣,他端着淬毒的匕首,眼睛都不眨的送進了自己的胸膛。
警笛聲撕裂了夜色中的寂靜和瘋狂。
警察來了。
可能是那個被我用九龍劍趕走的司機報的警,不過,當我出示萬金油一樣的黎明證件後,我們立馬從犯罪嫌疑人變成了座上賓,甚至,警察用警車把我們一路送回了京城。
路上,氣氛有些沉默。
良久後,大兵才在自己臉上拍了一巴掌,他很慫,舍不得用力打自己,然後他扭頭壓低聲音跟我說道:“小九,這事兒辦的惡心。
”
“确實挺惡心。
”
我想了想,很認真的點了點頭。
或許是我和大兵這種人是非觀真的有點扭曲,我總覺得該死的不應該是趙子良,而且還是被我們給脅迫逼死的。
但我不保證以後不會用更下作的手段。
力所不能敵時,就一定要用陰謀詭計和腌臜手段,這是我的人生信條。
陳瑤的情緒還是沒有平複下來,在車廂裡嗚嗚咽咽的哭泣着,最後惹得我也煩躁了起來,就扭頭對她說:“每一個白蓮花的身邊總有一個不知所謂的傻吊癡迷到底,收起你那如霧如夢的眼睛和如屎一般的浪漫情懷,我們的事兒辦的惡心,你更讓人惡心。
”
陳瑤果然不哭了,不知道是紮了她的心,還是不敢哭了,我也懶得問,最讓我納悶的是,初次見面時我還覺得她是個不錯的人。
人,終究是經不起深究的。
路上,我已經通知了安雅,任務結束了,黎明的飛機會在明天抵達京城。
等我們回到京城,并且找到下榻處的時候,天色已經蒙蒙亮了。
神經病又沉寂下去了,小豆子昏迷不醒,大兵和姬子的傷勢不是很重,不至于連夜去醫院,安雅也說了,黎明有最好的醫療條件,最好是回黎明治療。
我安頓照顧好大兵和姬子後,孤身一人離開了酒店。
秦教授的家在京城,我既然來了這裡,于情于理都該去他家裡看一趟,莫名其妙混到這一步,我還是有些不甘心,總是想着要去探尋一下因果,或許會有什麼能讓我撥雲見日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