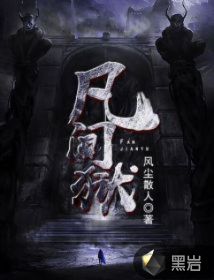人是種生而懼怕黑暗的生物,尤其是在知道自己身處險境的時候,對黑暗的恐懼尤烈。
我的精神世界陷入了黑暗裡,可因為這種極端的恐懼,又不敢沉沉休眠,心裡頭總有一個聲音在催促着我趕緊醒來。
迷迷糊糊中,我嘗試着睜開了眼睛,駱駝行走時上下颠簸,以至于我眼中的世界像攝像機正在被劇烈搖晃時的鏡頭反饋。
我正抱着一個人,準确的說,是我被綁在了一個女人身上,對方似乎怕我從駝峰中間墜落下去,特意用一根極粗的麻繩穿過我腰間,把我和她捆綁在了一起。
我正在趕路。
不等做出下一步反應,一條壯碩有力的手臂從後勒住了我的脖子,随即把一條髒兮兮的抹布捂在了我口鼻上。
濃烈的血腥味撲鼻而來,中間還夾雜着爛酒糟的氣息。
這種味道我曾經接觸過。
一個東北的熬鷹人曾經給我展示過這種東西,這是一種紅色的粉末,他們稱之為血腥香,人聞着很臭,會有嘔吐感,但是鷹和隼非常喜歡,混了酒放在地上氣味能揮發出很遠,鷹隼撲來就會被放倒,是一種強悍的迷藥,虎豹捏一撮塞嘴巴裡能昏睡三日,就算醒來半月之内也是渾身乏力,更不用說人,口鼻間吸入一些就倒了。
我掙紮了幾下,沒能掙脫那條腱子肉橫生的手臂,渾身卻越來越乏力,徹底被放翻。
販隼人回家的路很長
中間我又醒來過兩次。
一次是在梅朵給我喂酥油茶的時候醒來的,還有一次在路上,無一例外都被這些人用血腥香招呼了,第二次的時候丹巴似乎有些煩躁了,嘀咕說我反抗的意志太強烈,藥力太小沒什麼用,幹脆捏了點血腥香塞進了我嘴巴裡,從此我一睡不醒。
再次睜開眼的時候,我已經昏睡了好幾天。
入目處,是一個圓圓的屋頂。
這似乎是一座很大的氈房,裡面充斥着動物皮毛上特有的那種淡淡腥氣。
我躺在羊皮褥子上,雙目呆滞,腦子裡一片空白,如喪失了靈魂的行屍走肉,若非眼珠子間或滾動一下,隻怕任誰都會以為我隻是個高仿真的人偶。
長時間的昏睡讓我的反射弧快能繞地球一圈,幾乎喪失了思維能力。
良久,我才終于從久睡中回過了神,昏迷前的記憶碎片一點點拼接起來。
我在哪?
那些販隼人到底要幹嘛?
這些很要命的問題紛至沓來。
我掙紮着想要爬起來,卻渾身乏力,這是吞食了血腥香留下的後遺症,身子一歪,從皮褥子上滾到一邊。
哐啷!
放在我身邊的黃銅壺被打翻了。
“啊!
”
我旁邊傳來一道女性的尖叫聲。
我這才注意到氈房裡原來是有人的。
這是一個非常高挑的女孩,身高至少都在一米七五開外,身材纖細,光論體型而言,她絕對是頂尖的,就是形容狼狽的很,緊身牛仔褲已經很舊了,有些地方磨破了,褲子上到處是油膩留下的黑色污痕,油光锃亮,腳上穿着一雙愛馬仕的鞋子,不過鞋子很多地方已經脫膠開線了,上身則套着破舊的棉衣,披頭散發,整張臉都被頭發擋住了,隻能看見兩隻眼睛,像個女瘋子一樣
一個很奇怪的人!
這是我的第一印象。
她身上除了那件大棉衣,其他衣物鞋子無一不是最頂尖的名牌,我能瞧得出,這些東西絕不是高仿貨,一身行頭價值不菲。
能穿得起這些衣物的,哪個不是生活的光鮮亮麗?
可她呢?
在這充斥着寒冷和腥臊氣的氈房裡幹活,一身行頭不知道多長時間沒有換洗過了
我剛準備和她搭話,她看了我一眼後,低着頭立馬匆匆跑出去了。
我歎了口氣,很多疑問橫在心頭,又隻能放棄,躺了片刻開始四下觀察。
九龍劍不翼而飛,我身邊連把吃肉用的小刀都沒有,這幫人的警惕心還真大。
阿旺老漢很快就來了,一大把歲數,腿腳倒是很利索,拎着一個旱煙袋行步如飛,身上的羊皮襖子上落滿了雪花,剛一坐下來,我就從他身上聞到了刺鼻的旱煙味。
他對自己的形象不以為意,笑呵呵的在地上敲打着煙槍,問道:“你醒啦?
是不是在找你那把劍呢?
”
我點了點頭。
“我幫你保管着呢!
”
阿旺老漢一咧嘴,笑嘻嘻的說道:“等你和梅朵結婚了我就還給你。
”
“結婚?
”
我被吓了一跳,莫名想到了被擄那天梅朵的神情,似乎又在預料之中,不過我想不通那個女孩看上我哪點了?
“咋的,不樂意?
”
阿旺老漢揚起了頭,優哉遊哉的說道:“梅朵你也見過了,好看吧?
我們家的女孩都是這俏模樣!
你是被她馱回來的,快凍死的時候是梅朵抱着你的,清白都被你壞了,不嫁你嫁誰?
你們的婚禮已經在籌備了,過幾天就是二月十五了,就定在那天,按照我們這的規矩,結婚前新郎新娘不能見面,這幾天梅朵是不能過來看你了,你好好養身體,以後就在我們這部落裡跟梅朵好好過!
”
我想到了梅朵那張兩頰盡是高原紅的臉,長得倒是挺樸實,也很質樸,但漂亮似乎談不上吧?
不過這話我不敢說,鬼知道這會不會戳痛阿旺老漢那顆驕傲的心,讓他做出什麼沖動的事情。
我想了想,隻能借故說道:“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去辦,梅朵這事兒,我認,行不!
我辦完事準回來!
”
阿旺老漢咧嘴笑着,我又連續表達了好幾次自己有重要事情去辦的意圖,他都沒有反應,就像是聾了一樣,笑呵呵的給我規劃着我和梅朵婚後的美好生活。
他說,這是一片綠洲,水草豐美,很甯靜,是世外桃源。
他就是這裡的主人,梅朵以後也會繼承這裡,我會成為這裡半個主人,一輩子的幸福安甯是可以預見到的。
這死老漢裝聾作啞,我說了幾次算是看明白了,想讓他放我走基本沒戲,心思一轉,就打起了别的主意:“成,您這麼說,我就不扯淡了,我留下!
”
阿旺老漢以為我是被他的綠洲打動了,倆眼睛都笑的眯成了一條縫,連連拍我肩膀,贊道:“這才是好小夥子嘛,用你們漢人的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
”
“等等!
”
我叫住了起身準備走的阿旺,無力道:“我對梅朵并不了解,對你們也不了解,結婚是做一家人的,你們總得讓我知道枕邊的人是誰吧?
”
“我們啊?
我們就是一些行腳商人。
”
阿旺老漢笑眯眯的說道:“從藏北無人區到新疆,這一帶有很多牧民,他們生活困窘,對外面的世界又不了解,我們會把他們需要的食鹽、糖這些必要的生活物品送給他們,來換取一些牛皮羊皮之類的,再拿到外面去賣。
這樣的生活我們已經過了好幾千年了,現在社會雖然發達了,但好在還有很多地方過着原始人一樣的生活,我們的傳統倒也能維持,我們走的都是車子翻越不了的深谷荒漠,沒人搶生意,日子也滋潤。
”
編!
你特麼繼續編!
老子在内蒙生活過,現在羊皮有多廉價誰不知道?
前幾年光景最不好的時候一張羊皮五塊錢,幾乎沒利潤,你們的駱駝隊走深谷荒漠這種地方,辛苦自不必多說,還有性命危險,一趟就為幾百塊錢的皮子?
這是當我傻,就跟我沒看見你們籮筐裡的隼似得!
我跟看白癡一樣看着阿旺老漢。
果然,老家夥說到最後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輕輕咳嗽兩聲,又道:“好吧,這隻是我們一種生意,看你在青海湖附近獵的怪鳥,我估計你也是同行吧?
沒錯,我們行商的時候也會從牧民手裡弄點野生的東西過來,這才是賺錢的路子,要不綠洲裡大大小小百十口人呢,養不活!
”
說着,他站了起來,摁着我躺下,笑道:“你和梅朵結了婚,以後少不得發财的路子,你就安心先養着吧!
”
說完,老家夥背着手離開了,到了氈房外擺了擺手,我看見有兩個大漢頂風冒雪的趕過來,一左一右守在門口,就跟倆門神似得!
他一通軟話之後,終于露出了獠牙。
這擺明了是軟禁。
我哀歎一聲,輕輕閉上了眼睛,才出狼窩,又入虎穴,這是一個部落,有很多孔武有力的猛男,這回我該如何脫身?
想想梅朵那張紅潤的像富士蘋果一樣的臉,我打心眼裡膩歪,萬一晚上得對着那張臉睡覺,我就覺得胸口悶的慌,有點喘不上氣來
我忽然有點想念黎皇和黎明了
翻來覆去的在皮褥子上滾了一陣子,我開始思索逃出去的辦法,成與不成,反正這事兒我不能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