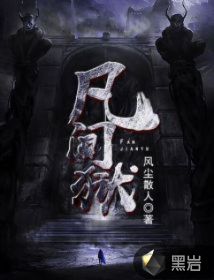每個人心裡總有一個俠客夢。
倒提三尺青鋒,一步一殺人,千裡不留行。
少年時誰沒有做過這樣的美夢?
長大後誰沒有被現實摁在地上狠狠摩擦?
直到被規矩、命運這些東西草的體無完膚時,才會老老實實把那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全部閹割,按部就班的活着。
九龍劍就在懷裡,劍鞘冷冰冰的,鋒芒被斂去。
我撫摸着劍鞘,心裡似乎有一頭野獸在掙紮着。
我不得不承認,雲溪撥動了我心裡的某一根弦,喚醒了我心裡的熱血,以及那個早已被撲滅的俠客夢!
“好!我帶你回家!”
我定定看着她,很認真的說道:“你是我見過最美麗的女人。”
“謝謝。”
雲溪笑的愈發燦爛了,明媚的甚至都有些刺眼,她愈是如此,愈是難掩笑容後的苦澀:“身子早就髒了,我都記不清被那些畜生碰過了多少回,從阿旺開始,到這裡的每一個男人,有時候洗澡我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擦掉,可總覺得髒,就是洗不幹淨,現在我忽然懂了,或許當我像個人一樣死去,埋葬在故土,我才能覺得自己幹淨。”
我沒接話,隻是把她背了起來,挪動她身子的時候,我觸摸到了傷口,那是拳頭大小一個血窟窿,就在後背,她能掙紮着跑到這裡已經是個奇迹了。
這是她在點燃藥倉時負的傷,她用老辦法賄賂了藥倉的管理,這才進了藥倉,那裡全都是丹藥,這個傻女人竟然在那裡點燃明火,爆炸時來不及逃出去,被炸起的破陶片擊中了後背,至于那個藥倉的管理,早被炸成了粉碎。
我用蟻人們包裹我的繃帶把雲溪捆綁在了背上,這才徐徐抽出九龍劍。
劍光潋潋,清淨如水,讓我心裡一片空靈。
儒以文犯法,俠以武犯禁。
我欲犯禁,像雲溪說的,做個俠客。
這與我一直奉行的保命原則背道而馳,可,那又如何?
人這一輩子總得返老還童幾回,做幾件少年時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部落裡仍舊隐隐可聞嘈雜聲,空氣中彌漫的都是火藥爆炸後的氣味,煙幕将夜空都籠罩了,讓這裡的一切都有種不真實感。
一個罵罵咧咧的大漢自藥倉的方向而來,似乎是敗下陣來了,這是阿旺老漢的一個親信,祭祀典禮上我看他親自操刀從一個老妪腹中剖出血淋淋的心髒,此時他心情很壞,與我撞個正着,見我背着渾身是血的雲溪,如何能猜不出我要幹嘛?獰笑一聲拎着馬刀向我迫來,大概是把我當成了撒氣桶。
我卯足力氣,無論是細胞還是腦域完全張開,爆出了最強橫的力量,直接一劍斬斷他的馬刀不說,九龍劍更是砍在他肩膀上。
他慘嚎一聲,跪倒在地。
我拔劍而起,一刀将他斬首,綠色汁液噴的很高,一直等我遠去後,屍體仍舊跪在地上,久久不曾倒下。
雲溪一聲不吭,隻是緊緊抱住我的脖子。
這注定是一條充滿血腥的突圍路。
藥倉那邊的争吵似乎有了結果,離開部落的路上,陸陸續續碰到數十人,無論男女老幼,全被我斬于劍下。
這是個肮髒卑劣的物種,我想不出讓它們活下去的理由。
部落外圍是一片白桦林,這個季節裡有些枯敗蕭索,是這片綠洲裡唯一的屏障。
當我沖出部落踏入白桦林的時候,雲溪似乎回憶起了什麼恐怖的畫面,下意識的抱緊了我的脖子。
“小心,小心!”
雲溪低聲道:“這裡有守林人,全都是部落裡最強大的怪物,以前有很多逃跑的人全都折在了這裡。”
我點了點頭,淌着積雪默默前行。
林子裡很安靜,安靜的讓人窒息。
咔嚓!
毫無征兆的,我腳下傳來一聲脆響,引起了我的注意。
林子裡雪很厚,走進來隻能聽到積雪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根本踩不到地上的樹枝。
我四下裡觀望一圈,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地方,略一猶豫,雙腿猛然發力,一聲長嘯向前竄去!
呼啦!
頭頂上有強風吹過,一個黑壓壓的東西幾乎是擦着我的頭皮掃了過去,那是一個捕獸用的木架子,上面全都是一根根削尖的木棍,要不是我躲避及時,被這東西拍個正着,恐怕會當場暴斃!
就地一滾後,我順勢站了起來,這時,難言的強烈危機感湧上心頭,背後又有激烈的破空聲響起。
我豁然轉身,卻見幾支利箭正朝我飛來,連忙抄起九龍劍“叮叮當當”将之掃落。
可惜,箭矢太多了,我躲閃不及,有一支箭矢以極其刁鑽的角度鑽進我腋下。
噗!
這一刹,我能聽到皮肉被撕裂的聲音,如果不是我及時用胳膊夾住了這支箭矢,恐怕已經傷及内髒,難以活命了。
這一切發生在電光石火間,飛矢木架,就是古老的捕獸手段,防不勝防。
白桦樹上有兩道黑影跳了下來,是兩個穿着白色皮袍的蟻人,他們身上有積雪,估計徹夜都在這裡埋伏着,部落裡都亂成了那樣,仍舊不挪窩。
“咦?”
一個蟻人輕哼一聲,冷笑道:“部落裡今天晚上不平靜,果然有人想渾水摸魚”
咔嚓!
我一把折斷肋骨處的箭矢,怒吼一聲率先朝這個蟻人殺了去!
對方也不是個慫主,從腰間抽出馬刀就迎了上來!
铿!
我一劍削斷他手裡的馬刀,眼看着劍鋒即将落在他身上,它卻猛然側身躲了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
見他躲避及時,我幹脆手腕一擰,變砍為削,一劍朝他胸口掃去。
噗!
蟻人的皮袍被我割裂,一時皮開肉綻,慘叫一聲。
可惜削終究不如砍威力更大,無法一劍将他斬殺。
我得勢不饒人,一步踏出準備一劍将之刺死。
可惜,我終究沒機會徹底結果了他,背後有勁風襲來,另一個蟻人看同伴吃虧,立馬動手了。
無奈下我隻能抽身阻擋,擋下這一擊後連忙後退,與這倆蟻人拉開了距離。
哒哒哒!
遠處有馬蹄聲傳來。
又有四五人縱馬趕來,隔着大老遠我都能瞧得見,為首一人,正是丹巴。
我這才想起,晚上他把我送回氈房後一直沒出現,原來在這裡守着。
這是個好手。
它身邊的這幾個蟻人也明顯比部落裡的蟻人強悍,全都是經過特殊訓練的。
我心下一沉,心知自己恐怕很難脫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