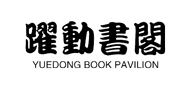第一卷 第476章:真是欠了他的
他心中愧疚,許了姬如玄三個人情,為免節外生枝,這三個人情,是通過太尉府俞家許下來的。
姬如玄靠在椅間,喘了一口氣,虛弱道:“當年,萬君山曾許我三個人情,其一當初請玉衡子出山,為穆貴妃診治,已經用掉了。”
樞機子暗暗歎氣,打開玉盒,裡頭裝着褐黑色膏脂,散發出一股濃重的藥香,這藥香一點也不難聞,透着一股草本天然的清苦,光是聞一聞,就叫人精神不由一振。
姬如玄鈍痛的腦袋,也不由為之一清:“還有兩個人情,其一,請道長親自出面,保下長公主,其二,請萬君山照拂長公主三年。”
樞機子爽快道:“這不難辦,貧道應下便是。”
姬如玄心弦一松,忍不住咳了幾聲。
“瞧你這半死不活的樣子,”樞機子一臉肉疼,取了一勺膏脂放入杯中化水,遞給了姬如玄,“快喝,快喝,你知道這藥有多名貴麼?千年人參,初生幼鹿的幼茸,産自黃海的海馬,産自胡羌一帶的鎖陽,沙漠一帶的肉從蓉等,一百多味産自道地的藥材。”
道地藥材,是在特定自然條件、生态環境的地域内所産的藥材,同種藥材,道地藥材品質更佳、療效更好。
甭看這一小盒藥材,光是藥材就是天南地北,天上飛的,海裡遊的,地裡長的,千奇百怪。
搜集藥材之時,要挑采集的時節、天氣、時辰,挑選年份最佳,藥效最好的藥,一些藥要在海裡打撈,十分不易,還有一些藥,要在沙漠上去采,環境惡劣,玉衡子搜集了幾十年,也就做成了這麼一盒龜令秘藥,是道家養生的瑰寶。
“多謝。”姬如玄從善如流,接過杯盞,一飲而盡,溫鹹的滋味沿着喉嚨,滑入腹内,令他有一種沉苛盡去,枯木逢春,渾身松快的感覺,僵冷的身軀,頓時有了暖意。
樞機子道:“你體内的殘毒每發作一次,便兇險一分,經過這一次反噬,殘毒又強勢了幾分,散功攻毒,已經不能克制,最好的辦法,是趁此機會散功袪毒。”
姬如玄沒有就話,神情卻有些無動于衷。
“你這臭小子,”樞機子忍不住罵了一聲,“如果你答應散功袪毒,我以龜令秘藥相助,至多五個月,就能助你袪毒成功,功力恢複到巅峰狀态,保你将來長命百歲。”
提及龜令秘藥,他吸了吸氣,肉眼可見的肉疼。
若沒有龜令秘藥相助,這毒至少要一年才能袪完,至少大半年,不能妄動真氣,且袪完毒後,還要花半年時間休養,功力才會恢複至巅峰狀态。
姬如玄嗤笑一聲,倒也不是諷刺什麼,隻是覺得,五個月不能妄動真氣,對現在的他來說,是根本不太可能。
如果長命百歲隻他一人,他甯可不要。
姬如玄看着他,斬釘結鐵道:“三年後,我必再登萬君山,請道長助我驅毒。”
樞機子罵罵咧咧的:“你這人,怎麼是個死腦筋,我都答應你了,會出面保下長公主,你急什麼?小子,人一急,就容易犯錯,你可不要急功近利,枉造殺孽,到時候業障纏身,不得善終,而且就你現在這破身子,能不能撐三年,還尚可未知,你可不要因小失大。”
姬如玄沒說話,他知道樞機子有能力保姜扶光安康,但能保多久,誰能知道?
他是絕不會把姜扶光的性命,交給其他人去掌控。
“煩死了!”樞機子拿他沒辦法,又是一通罵罵咧咧的,從玉盒裡挑了核桃大小的膏脂,裝在另一個小玉盒裡,偏開眼睛,猛推到姬如玄面前,一副眼不見,心不煩的神情。
“每次散功攻毒,或餘毒有反噬迹象時用一些。”
姬如玄的看向樞機子面前巴掌大的玉盒。
“看什麼看,”樞機子立馬将玉盒撈進懷裡,用防賊似的目光看他,“隻有這麼多,沒有多的了,想也不要想。”
想到今兒舍了小半,剩下大半,說不準三年後,還要用來給他袪毒,樞機子就一臉崩潰,悲從心來。
真是欠了他的。
……
咳。
咳咳。
姜扶光臉色蒼白,靠在迎枕上不住地咳嗽,璎珞端着藥進了屋,見長公主又在咳,心裡不禁一陣擔憂。
長公主醒來後,身體一直很虛弱,太醫說,長公主凍傷了身子,落了病根,難以根除,如不趁着年輕好好靜養,甚至會折損壽元。
她斂下眼中的擔憂,伺候長公主喝藥,便又說起了宮中的消息:“今日一早,榮郡王召見了朝中撰史的官員,要求翻閱史書被拒,榮郡王勃然大怒,史官卻直言道,帝王不可躬自觀史,此舉有違古制及祖訓,不符合規矩。”
姜扶光又咳了兩聲,啞聲道:“史館現在撰史官員,是南史氏,他們以春秋齊國南史氏後人自居,家族之人,世世代代為史官,記錄曆朝曆代的朝堂大事。”
史官都是家族世襲,通常是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整個家族所有成員,都可以成為記錄史書的官員,因此又被稱為“史氏”。
春秋時期,齊國大臣崔杼,殺了主君齊莊公,崔杼為了掩蓋曆史,找到了齊國當時的史官太史伯,要求他更改史書記載。
太史伯不受威脅,在史書上寫下了“崔杼弑其君”,崔杼勃然大怒,當即殺了太史伯。
崔杼又相繼找了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三弟、四弟太史季,殺了一個又一個,崔杼的心态徹底崩了,行吧,你們愛咋寫就咋寫吧,就算把太史家全都殺光了,朝中還有其他史官,也會如實記錄一切。
當時的南史氏,聽聞了太史氏的遭遇,立即程車,準備代替太史家寫史,在路上聽說崔杼改變主意了,這才打道回府。
君舉必書,秉筆直書,不懼生死,是‘史氏’家族,世世代代傳承的精神,家族裡每一塊牌位,都是祖宗不懼生死,秉筆直書的豐碑,不忘祖訓,乃孝之大也,後代子孫,毫無例外都保持了這種初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