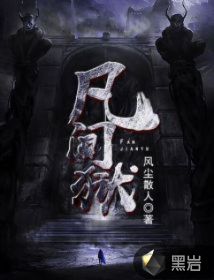日子又恢複了前幾天的模樣。
雲溪照常還會來,她再沒有和我說話,表現的和初見時差不多,不過每次她來,總會在收拾屋子的時候悄無聲息的從懷裡摸出一些食物塞到被褥下面,然後默默端起夜壺離開。
食物永遠是熱的,也永遠都是油膩的,在這寒冷的地方,必須要攝入足夠的熱量才能保證自己的體能,就是苦了她的皮肉,不知道被燙成什麼樣了。
我更不敢問的是這些食物從哪裡來。
第一次是偷得,那麼第二次、第三次呢?
總是偷食物,難免會被發現,到時一切謀劃前功盡棄,雲溪不會那麼蠢。
她隻能去換。
天知道我每吃下的一口食物,到底是她經曆了怎樣的痛苦才換來的。
她隻能用一樣東西去換。
我心裡跟明鏡兒似得,可就是不敢問,就怕問了沖出去拼命,最後把倆人都交代在這,幾乎是明火執仗的裝聾作啞,有時候窩囊的喘不過氣就用被子蒙着頭吼一兩聲來發洩。
趁着守衛不注意的時候,我用掉了第二顆“丹藥”。
火藥燃燒時的刺鼻的味道驅散了我體内的所有匮乏。
我的力量終于開始複蘇了,之前身體仿佛不是自己的,感受不到身體上的一切,現在我能清晰的察覺到躍動在細胞内部的能量,這讓我很有安全感。
沒有九龍劍,我的力量等于被削去了一半,九龍圖上的很多招式都需要這把劍才能指引出來,現在我隻能靠自己,萬事都得慎之又慎,我開始刻意去觀察這個部落裡的怪物。
到現在為止,我仍舊不确定它們到底是什麼物種。
靜下來後,我努力的回憶黎皇的收藏館裡的資料,有類似生育崇拜和祭祀習俗的怪物有不少,光靠雲溪所說的信息還不足以确定我的對手是誰,除非它們露出本來面目,我必須去了解它們,否則動起手來容易吃虧。
幾天觀察下來,我發現它們并沒有我想象中那麼強悍。
它們的身體素質很好,尤其是抗擊打能力,肌肉壯碩,力量也不小,骨關節極其粗大,唯獨脖頸的位置,那裡大概是它們最脆弱的地方。
當然,也有幾個厲害的,譬如丹巴。
青海湖畔它撂倒我時候那一拳頭昂我記憶猶新。
好在,這樣的人不是很多,在這些男人裡處于領導地位。
我通過雲溪邀請來了丹巴,理由是和他很對胃口,覺得他是個勇士,閑的沒事,想和他喝酒。
這家夥蠢笨如豬,腦子裡都是肌肉,最喜歡别人誇他勇武,一瞬間飄得找不着北了,白天的事情剛剛忙完,夜幕初上時就拎着烈酒來找我了。
隻要我不走出氈房,這些怪物對我的态度很友好。
沒人會仇恨一個即将燃燒自己為它們種族續命的人。
我和他喝了一整夜,對他的了解更多了。
相比于其他怪物,丹巴撇開力量和抗擊打能力這些種族天賦以外,唯一的優點就是速度比較快,這得益于後天的鍛煉。
當一個人的肌肉非常發達的時候,意味着他的爆發力會很強,如果專注于鍛煉,速度快不是很難。
我覺得如果我全神戒備,并且打開腦域的話,要捕捉他的動作不是很難,費點力氣應該能弄死他。
對對手有了評估後,我安心蟄伏,見人就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樣子,病恹恹的,阿旺老漢來看過我一次,對我這種狀态很滿意。
很快,二月十五到了。
這一天,一大早外面就傳來爆竹聲,很熱鬧。
梅朵的婚禮是今年最盛大的婚禮,她是阿旺老漢的嫡系子嗣,跟阿旺老漢很親近,部落裡的人對她寄予了極高的希望,覺得她的繁衍能力一定不會比阿旺老漢差,肯定能為族群開枝散葉的。
我第一次離開了氈房。
守門的兩個壯漢把我架了出去,圍繞着部落轉了三圈後,又把我拎了回去。
這是他們的習俗。
這是個将近一百人的部落,居住在一片小小的綠洲裡,四周的白桦林已經枯萎了,一片小小的湖泊完全結冰,那是維系這裡的唯一水源。
這裡女人很少,轉了一圈,我隻看到十幾個,剩下的全都是男人,一個個體魄壯碩,都能謂之彪形大漢。
它們這個族群的繁衍問題确實令人堪憂。
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像雲溪一樣的女仆。
雲溪說過,這個小部落每年都會捉很多女人回來,但基本上不是被折磨死了,就是瘋掉了,活下來的很少,人一批又一批的換着,但打她來這起,好像就這七八張面孔一直都在,神經堅韌的人終究是少數。
女人們湊在一起,對我指指點點,評頭論足,就像是在評估一頭種豬,從她們的表情上能看得出,她們似乎對我很滿意,不少女人還擠眉弄眼,丢給我一個“你懂得”的眼神。
倫理在這裡不重要,羞恥也不重要,繁衍最重要。
可惜,我一點心猿意馬的感覺都沒有,這裡絕不是男人的天堂。
我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怪物種族,但它們幻化成人形後的樣子絕對稱不上美麗,女人們大都是一張中年村婦的面孔,身材臃腫,因為強烈的紫外線和狂風摧殘,臉上的皮膚呈現出一種绛紫色,法令紋特别深,咧嘴一笑,滿嘴的牙齒就像是一排碼的整整齊齊的黃色玉米粒。
我覺得阿旺老漢真的是個狠人,面對這種貨色都能解開褲腰帶。
能想象這是一個怎樣的畫面麼?
一群村婦跟着你,一路上不斷往嘴裡丢瓜子,“噼裡啪啦”磕完後,瓜子皮混着口水耷拉到下巴上自然墜落,同時一個個還眉眼婉轉,渾濁的眼珠子轉來轉去給你丢眉眼
你覺得這叫男人的福音嗎?
如果這都算,我隻能說,兄弟你太特麼狠了。
反正我是受不了,等守衛把我拎回氈房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梅朵似乎也不是那麼難以接受了,至少和這群老娘們比起來她絕對是國色天香。
按照這群怪物的習俗,婚禮當天是不進食、不見客。
我被餓了一整天,就連雲溪都沒有來,我不知道她是否做好準備了,隻能在心裡祈禱一切順利。
轉眼,月上枝頭。
大概在晚上八點鐘的時候,氈房外面沖起了火光。
我被吓了一跳,以為雲溪已經動手了,差點從皮褥子上跳起來,不過很快我就聽到了外面男男女女的歡呼聲。
儀式開始了。
丹巴帶着兩個擡着擔架大漢的興匆匆的跑了進來,對着我咧嘴笑道:“兄弟,你的好日子來了,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
說完,他擺了擺手。
兩個大漢沖上來就把我放上了擔架,不等我反應過來,他們拎出冗長的白绫開始往我身上纏,不過片刻我就被綁成了一具木乃伊,隻剩下一顆腦袋還在外面,動彈不得。
丹巴撫摸着我身上的白绫,咧嘴笑道:“我們崇拜白色,這是最喜慶的顔色。”
果然獨特!
我們用來送死人的東西,你們用來迎新人。
我心裡在冷笑,這麼捆綁讓我覺得自己像闆上任人宰割的肥魚。
“好好對梅朵!”
丹巴拍了拍我的臉,又做了幾個男人都懂的下流動作,嘿嘿笑道:“她可是我們這裡最美麗的女人!”
說罷,他一擺手,兩個大漢擡起擔架就向外走。
我看着丹巴高大的背影,眼中閃過一具不易察覺的冷光。
所謂婚禮,應該是群魔亂舞才對。
估計很快我就知道它們到底是些什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