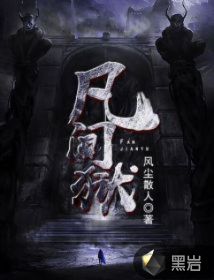裴繼安“哦”了一聲,表面若無其事,心中已是有如一萬隻螞蟻在亂爬,那螞蟻還隻隻都多長了八條毛毛腿鈎來鈎去,爬得他心癢難耐,又想問,又要端着,偏不好問。
他憋了半晌,忍不住道:“煮的菜湯嗎?”
鄭氏看在眼裡,也品出了一兩分味道,便搖頭道:“叫我在外頭等,也不肯說,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裴繼安坐在堂中,也不說回房換衣裳鞋子,隻把手上提的東西一放,道:“她火都不會生,一個人在裡頭,定是笨手笨腳,我去瞧瞧,省得把葉子煮黃了都不曉得。”
口中說着,已是往大步廚房走。
鄭氏隻抿嘴笑,并不攔着。
裴繼安的擔心并不是多餘。
沈念禾那一鍋湯已經煮得七七八八,雖然不至于把葉子都熬黃了,可嘗那味道,實在是出乎意料的奇怪。
她聽得外頭聲響,轉頭見到裴繼安,吓得忙用蓋子把鍋蓋了,叫道:“三哥甚時回來的!且去外頭等着吃晚飯罷!”
裴繼安并不回她,而是指了指下頭的底竈,道:“火要熄了。”
沈念禾一驚,低頭一看,果然方才自己添柴沒添好,已是把原本的火都壓黑了大半,連忙彎腰去拱火。
裴繼安就走得近了,道:“小心被炭星子濺上。”
他沒來時沈念禾已是手忙腳亂,他來了之後這一番指點,叫沈念禾更是手腳都亂得不知道怎麼放。
裴繼安就把她支使到一邊去看菜,自己撿張小幾子坐下來幫着看火。
他身高體壯,即便是局促地蜷坐在小幾上,隻要一擡頭,依舊能平視看到鍋裡的東西。
人都坐下了,自然不好再趕走,沈念禾隻好把鍋蓋掀了,老實承認道:“三哥莫要笑話——我本要煮魚湯,隻是沒煮好。”
裴繼安聽得是魚湯而不是什麼菜湯,心中已是有了十二分的滿意,溫聲道:“我聞着很清香,哪裡沒煮好了?”
沈念禾就指着那一鍋道:“我已是下了姜同蔥白,隻是不知道為什麼,魚腥味還是很濃,另有橘皮絲也搶了味。”
她語氣裡頗有幾分沮喪。
裴繼安就站起來看那正滾着的一鍋。
湯是清湯,用沒有煎過的大鲫魚炖出來的,湯中還放了菘菜,菜煮得已經十分軟爛。
這樣一鍋沒有賣相的,拿出去館子裡,除非倒貼錢,不然恐怕沒有人願意吃。
沈念禾歎了口氣,道:“我想着三哥不愛吃味重的,就不煎魚了,打算煮清湯。”又指了指一旁的空碗,“本是用白蘿蔔切蓉揉出汁,再下橘皮絲,又解腥,又增清香味,誰知那蘿蔔汁又苦又辣,橘皮絲也澀,混着魚湯,味道奇奇怪怪的。”
頭一回做菜,菜式還做得這樣異想天開,能好吃才怪。
不過對于裴繼安來說,好不好吃本來也無所謂,他拿湯匙舀了兩勺,又用筷子搛了一塊魚肉并一片菘菜葉出來,一一嘗了,連眉頭都不皺一下,隻道:“魚肉很炖得很好,也清淡,那菘菜也嫩——你把外頭葉子都剝了?”
沈念禾哪裡肯信,隻道:“三哥是哄我罷?這樣難吃,不要硬撐了。”
裴繼安當真不覺得很難吃。
他從前出去做生意的時候,幹硬得跟石頭一般的餅也吃過,可能是因為放得久了,味道還發酸,相比起來,這樣特地給自己做的一道湯,色色都十分用心,哪裡難吃了?
為了表示自己并不嫌棄,就着這一碗湯菜,當晚他比平日還多吃了一碗飯。
沈念禾卻有些受打擊,覺得這是裴三哥為了自己面子,再不合胃口也要硬咽下去,再不敢随便進廚房了,隻幫着鄭氏打打不要緊的下手。
鄭氏在一旁看着,卻是琢磨出些意思來,跑去勸裴繼安道:“我廚藝不行,你平日裡做菜也帶帶你沈妹妹,好歹學得幾手,将來出嫁了也不至于叫公婆嫌棄。”
裴繼安的臉一下子就黑了,道:“當真嫁得個小門小戶,她那丈夫難道竟是不會做?怎的要她來做?”
又道:“什麼公婆,這也要嫌棄?我自幫她選,不會挑個那樣不靠譜的——若不是不好太打眼,我都想雇個人回來看廚房,等我不在的時候,也不必叫嬸娘下廚,煙熏火燎的,又有刀。”
言下之意,嬸娘都不想叫做飯,沈妹妹自然也不能做飯。
裴七郎在的時候,确實從來沒有叫鄭氏下廚過。
倒是裴繼安的親娘有一手好廚藝,隻是也極少顯露。
鄭氏抿嘴笑了笑,也不說旁的,隻問道:“左近哪裡有那樣好的人家?”
裴繼安毫不在意,道:“念禾還小呢,不着急,等我起來了,什麼好的給她找不到?”
鄭氏看着裴繼安長大,對這個侄兒的能耐很有信心,自然不會認為他起不來。
隻是她冷眼看着,面前這一位已是由從前的“若有那一日,嬸娘幫着給沈家妹妹看個好的”,變為了“我自幫她選”。
卻不曉得等他起來了,又會變成什麼樣。
鄭氏見侄兒的身材應當不怕食言而肥,便也懶得說什麼,隻當做一出長戲,有滋有味在一旁看着。
倒是沈念禾被蒙在鼓裡,哪裡曉得這嬸侄兩個已經就自己的婚事讨論過好幾回。
她做了難吃的菜,再不敢輕易嘗試,想着當日裴繼安說要鬥笠同披風,因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手藝實在上不得台面,特地跑去同鄭氏把事情說了,又道:“我見外頭鬥笠都長得差不多,全是隻遮雨遮雪的,半點不擋風,冷嗖嗖的,本想拿棉花同棉布縫個内襯,隻是上回試過了,樣子十分醜,連針腳都東歪西倒的,不如還是嬸娘來弄罷?”
鄭氏也沒多想,果然選了棉布,估計着裴繼安的尺寸,不要小半個時辰,便把棉花縫了進去,針腳細密不說,還把那鬥笠上上下下整理得十分整齊。
沈念禾看着她飛針走線,做得出來的東西同自己給謝處耘的那一個簡直天差地别,不禁由衷贊道:“嬸娘做得這樣好,三哥戴着必定十分合用,不知道得多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