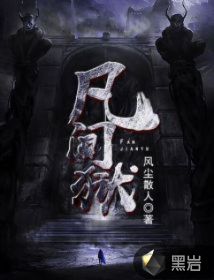周承佑自受傷之後,病情反複,傅皇後心疼兒子,很快就将他從東宮挪入清華宮,一來方便照應,二來也又有防備他人窺視的意思。
然而自從上回同天子面見之後,周承佑便又從清華宮搬回了東宮,不僅如此,周遭伺候的人早全數換了一輪。
周弘殷進得東宮,也不着急去看兒子,隻轉進一處偏殿。
此時早有黃門官綴在後頭跟了上來,見得天子坐于桌案之後,連忙立在下方等着問話。
果然沒過多久,便聽周弘殷道:“此處可有抄檢出什麼東西?”
那黃門低眉順眼地道:“回禀陛下,旁的地方倒是幹幹淨淨,隻是這書房當中查出些許東西,臣拿不準,已是封存起來……”
他說着,卻是取了鑰匙,從一旁的櫃子搬出一個不小的匣子來,當着周弘殷的面打開,裡頭層層疊疊,或是奏疏,或是往來信件,也有些稿紙。
周弘殷伸手結果,将其中東西攤開放置在桌面上一一檢視,越看面色越是發黑,到得後頭,整張臉便似鍋底一般。
那黃門察言觀色,哪裡還敢說話,隻屏氣凝神不提,心中卻是有些惶惶然。
東宮早已被查過兩回,頭一回因為沒有查出什麼東西,後一回因為查出太多莫名之物,統管之人全被天子治了罪。
幸而有了前人做示例,他才好斟酌着來辦,隻是一時猜不透上意,也拿不準尺度,想到前次兩人下場,唯恐自己步入後塵,此時難免兩股戰戰。
周弘殷速度極快,不多時就将桌上文字翻撿完畢,複又冷聲問道:“便隻有些許文書,竟無旁的東西?”
黃門忙道:“下官已是搜查數遍?其餘俱是幹淨得很?隻是另有一樁,聽聞這兩個月東宮裡頭已是無人居住……隻是到底是清華宮……”
言下之意?太子不住在東宮久矣?便是真有什麼不妥,也未必能在此處查得出來。
他不敢口稱太子?想了想,索性将事情推到傅皇後頭上以觀望一二。
果然?周弘殷并不因為提及清華宮便有半分阻滞?而是語帶肅然地道:“既是已然知曉,怎不早早報來?!”
那黃門立時跪于地上請罪不提。
周弘殷也不理會其餘,徑直站起身來,轉身便往外走。
他速度并不快?走起路來甚至腳下都有些虛浮?可步伐間并無半點猶豫。
黃門哪裡料到天子隻問幾句,匆忙膝行了一段,道:“陛下!東宮……”
周弘殷聽得聲響,卻是連頭也不回,足下半步不聽?自行走了,留下那黃門官一頭一臉的汗?隻覺得全身都被吓軟了。
他此刻撿回一條命,心有餘悸?擡頭看着殿門外守衛森嚴的禁衛軍,卻是連爬起來的力氣都沒了。
天子來得東宮?隻問了一通查問情況?全無意思去見太子。
天家父子相殘也不是什麼稀罕事?可像如今一般,半點不避諱他這下頭辦事的喽啰,卻是擺明已經要撕破臉了。
黃門官坐着坐着,也不知道是地面鋪的金磚太過冰寒,叫他由屁股涼到了全身,還是心中的冷意蔓延開來,當真是手腳冰涼,坐立不能。
内侍最怕宮中起變,尤其他這等手頭并無半點權勢的,一旦出得事,不管誰人上位,又是個什麼結果,少不得要他這個知情者來陪葬。
***
周弘殷出得東宮,直取清華宮。
傅皇後聞訊早早就出門相迎,可還未行等完禮,周弘殷已是越過她先行進了殿中,扶桌坐于椅上,也不說話,先緩了兩息,才同跟來的黃門官道:“去把西邊收拾收拾。”
那黃門急忙領命退去。
傅皇後跟得進殿,面上神色不定,視線卻是忍不住跟着那黃門往外走。
周弘殷見她這模樣,忽的道:“西邊宮殿裡頭,平日裡都是些什麼人出入?”
夫妻幾十載,早些時候或許還有些患難之情,然而至于今上繼位之後,一則打壓、冷落傅家一脈,從不給皇後面子,二則他本就是個莫測反複的性子,前幾年重病之後,更是變本加厲,已經不是簡簡單單“不好伺候”四個字可以形容。至于後頭寵信星南大和尚等人,惡言駭行,屢屢不絕。
所謂伴君如伴虎,全然沒有說錯。
傅皇後戰戰兢兢多年,原來還小心應對,後來發現多做多錯,少做也錯,哪怕不做都會被盯着,哪裡還不曉得自己是礙了眼,可彼時天子大權在握,而自己家中已無多少助力可言,又兼兩個兒子漸長,也并非沒有憑恃,隻好強忍着同丈夫耗下去,看誰人命長。
眼下看到周弘殷此刻行事要拿兒子開刀,絕無可能善了,她也再懶得陪小心,而是冷笑一聲,道:“妾身這清華宮中一言一行不都在陛下眼目之下,至于西邊宮殿,更是早有禁衛看管,陛下此刻來問,妾身哪裡知曉,不如問自己來得快!”
周弘殷勃然大怒,喝道:“豎子如此賊逆之心,全是你這賤婢養出來的!”
他氣力不足,聲音裡頭還透着幾分虛弱,可罵起人來臉上表情扭曲,語義更是尖酸刻薄,全不似天下之主。
縱使傅皇後對待丈夫時,一顆心早已如同枯木,此時聽得他如此辱罵,口稱“賤婢”,卻是不免色變,隻到底知道兩人不同尋常夫妻,又當此之時,哪怕為了兒子,再多的氣也都隻能咽下去,索性捏着拳頭,閉口不言。
周弘殷正在氣頭上,又如何肯放過,旋即厲聲喝問道:“那小子平日裡私勾大臣,暗藏違禁之物,不忠不孝,難道當我是個死的?!”
罵自己時,傅皇後可以不做理會,可罵到兒子頭上,還冠上“不忠不孝”這樣的帽子,她卻是再不能隻是聽着。
大魏以孝治天下,更遑論周弘殷是君又是父,他有此權威之位,當真要在外人面前說周承佑不忠不孝,又有心逼迫的話,未必不會逼得兒子以死明志。
她當即大聲駁道:“陛下何出此言,承佑眼下才幾歲?他平日裡忠君孝順,無論是于朝于國,還是于孝悌一道,哪裡做得錯了?”
又道:“至于什麼‘違禁之物’,難道他竟不是太子?!他如此年輕,哪裡就差這一點了?!”
這話不說還罷,一說之後,渾如火上澆油。
周弘殷自上而下甩出一本折子到地上,那折子沒有鎖邊,嘩啦啦的白紙一下子跌開,露出裡頭密密麻麻的字迹,半張在傅皇後前頭。
“須叫你死的不冤!”
他冷冷道。
傅皇後不怒反笑,也不去撿那折子看,而是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何況這小小的禁宮當中,陛下說是便是,還有什麼可查的?”
又道:“妾身隻歎承佑,自小上進,滿腹孝悌之心,卻被小人所誣!”
她指着地上折子,質問道:“事到如今,我隻問陛下一句——難道承佑就當真等不得這幾年嗎,難道這大魏不是子承父位,竟要他兵行如此大逆不道?”
周弘殷冷冷道:“你母子二人,早以為我活不得幾年了吧?”
傅皇後情急之下張口說話,氣沖于腦,哪裡想得那樣周全,被周弘殷尋得其中一處錯處問,卻是一時語塞。
若說不是,着實又是她心中所想,遮掩不得,若說是,又如何能說。
周弘殷冷哼一聲,道:“若我一向不死,你母子二人,又奈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