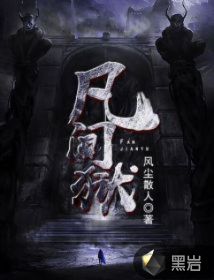靈咒到底是個什麼?
姬子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個所以然,他不善言辭,正在竭盡所能的用嘴皮子來诠釋一件玄之又玄的事兒。
我聽得抓耳撓腮,細細思索他說的話良久,沉吟道:“一種類似于詛咒的東西?”
姬子忙不疊的點頭。
“你信?”
“由不得不信!”
姬子搖頭晃腦的說道:“民間的詛咒是個什麼玩意?不外乎就是巫蠱之術而已,把名兒和生辰八字寫到小紙人上用針紮?那都是無稽之談,不信找個神婆讓他來紮我,她要真能把我紮死,我絕無怨言!
可這些邪物的咒不一樣,真的會死人!
我隻能說,這些邪物的詛咒是目前黎明理解不了的層次,或許是一種非常神秘的力量?但它确實存在,黎明裡多少名宿悍将都是死在了這種詭異的手段上,很冤!”
說此一頓,姬子垂下了頭,輕歎道:“我家裡就有一位長輩就是這麼死的,他是被一個邪物給活活拜死的,那位長輩修行已達涅槃秘境的極限,往前一步,或許就能踏入另外一個維度,結果被一個邪物雙手持香,對着他就是那麼輕輕一拜,天上立即雷霆滾滾,活活把那位長輩劈成了焦炭。”
我聽的寒氣直冒,忙問:“這種詛咒是一部分特定的邪物種類才有的本事?還是”
“你懷疑我謊報情報?”
姬子粗暴的打斷了我,他咬牙道:“靈咒隻有靈懂,靈在邪物中本身占的比例就很小,而且不是什麼靈都懂這玩意,這東西全靠天賦,或者全靠命,一萬隻靈裡最多最多隻有一隻會意外覺醒靈咒,而且它們的靈咒未必強橫,多數都是拿不出手的,能咒死人的靈少之又少,一百萬個裡冒出一個就不錯了!”
覺醒
現在我聽到這倆字兒就覺得頭皮發顫,這些邪物一言不合就覺醒了,誰也不知道它們的基因裡到底藏着多麼可怕的力量,好像永無止境似得。膽小懦弱的龅齒犍能搖身一變成為強悍的戰士,都刷新了黎明的認知,以至于現在龅齒犍也被列入黎明必殺名單裡了。
這回,我們又碰到一個,誰也沒料到顧知白會有這樣的手段,全部中招,一個沒跑。
“那顧知白的靈咒能不能咒死人?”
我滿含期待的問。
“你以為他說拉幾個墊背的是在吓唬你?”
姬子毫不客氣的撲滅了我希望的火光,仿佛被靈咒了的隻有我似得,他一點都不擔心自己的性命,淡淡說道:“他的靈咒一出,陰風怒号,天地色變,這種級别的靈咒要是再咒不死人的話才見鬼了。”
“除了黑霧穿胸時莫名的感覺害怕,我再沒察覺什麼異常。”
我道:“應該不會有大問題。”
“靈咒殺人,豈是尋常途徑?”
姬子冷笑道:“你以為隻是天打雷劈嗎?受了靈咒,會有三災五刑降臨,雷屬陽,算火,我家的長輩遭的應該算是是五刑之中的火刑,已經是死的比較利索的了!”
所謂三災五刑,便是被靈咒咒了的後果。
三災說的是戕殺、瘟疫、饑馑,五刑則是金、木、水、火、土五種屬性的刑罰。
受了靈咒,三災五刑必受其一,抗的過去就算命硬,抗不過去挑個風水寶地埋了就是,轉世輪回這些虛無缥缈的事兒就别想了,涼了就是涼了。
我整個人都不好了,橫禍懸頭,還不知什麼時候會落下來,這滋味最難受。
“你有九龍劍!”
姬子冷冰冰撂下一句,從雪地裡爬起來就走。
這就是屁話!
我心裡暗自咒罵着。
回去的旅途是漫長的,一段行程下來,靈咒的事情漸漸被我們抛諸腦後。
好景不長,就在我們幾乎要從巨大的陰霾下掙脫出來的時候,橫禍毫無征兆的降臨了。
老A死了!
走出莽莽大山,越過淼淼牧區,就在我們剛剛進入一個不知民的小村莊的時候,一輛轎車疾馳而來,在隻夠一線單行的狹隘土道上,車速超過一百邁。驚慌之下,我抱起小豆子躲到一側,大兵和姬子反應速度也很快,唯獨老A像失了魂兒一樣站在道路中間。
我喊過他,非常大聲的提醒過他。
可他沒有避開,反而扭頭沖我笑,笑容像小時候在家鄉常見到的那個總被一群孩子滿大街追打戲弄的傻子!
慘劇就這麼發生了。
哐的一聲,轎車停下了,老A被撞得飛上了天,落地時,他那顆老是被我打來打去的光頭結結實實的撞在了冰冷的地面上,然後像西瓜一樣“啪”的一下子炸開了!
血和腦漿甚至飛到我的褲腳上。
車上沒人,那是一輛無人駕駛的轎車,撞飛老A後就那麼名目張膽的停在我們面前。
小豆子打開了地靈眼,這一次任務她頻繁使用地靈眼,已經超過承受極限了,再次睜開眼睛的時候,雙目正在滲血,但她還是很努力的試圖搜尋一些肉眼看不見的東西。
可惜沒有。
這種死法擊垮了我們的心防。
老A為什麼不躲?車為什麼在無人駕駛的狀态下能沖出來?
我不知道這茫茫天地間是不是真的有神靈或未知力量這麼一說,如果這樣的力量讓我們死,我們這些渺小的生靈如何能抵抗?
事發後,我們四個人的表現出奇的一緻,捂着頭靠着農舍的土牆蹲了下來,我的腦子裡一片混沌。
村裡一個穿着棉衣、體型看起來像棗一樣臃腫的女人拎着鐵鍬賊頭賊腦跑了出來,看了我們半天,發現我們沒别的表示後,抄起鐵鍬要鏟走老A飛濺的滿地都是的腦漿。
這些荒野村落的人封建蒙昧,現在還有人覺得人腦有用,每次發生車禍,總會有膽大的來鏟腦子為自家營收。
大兵爆發了,抄起石頭要打死中年婦人,對方吓得夾着鐵鍬落荒而逃。
很快,村子裡沖出很多人,他們拿着榔頭、斧頭,叫嚣着要弄死我們,我們四人渾渾噩噩倉皇逃了出來。
離開前我扭頭看了一眼,村子裡很亂,有人追打我們,有人急着要蘸人血饅頭。
我們一直跑到村外的林蔭小道時,身後才總算沒了人,一個個氣喘籲籲,渾身發軟,不是累得,其實是被吓得。
“車屬金,這應該是金刑!”
定了定神,姬子給這件事下了論調。
“誰還管這個,我特麼就知道前兩天還跟咱說笑吹牛的人,一轉眼莫名其妙的就死在老子面前了,你們看見了沒?老A腦袋爆開的時候,前臉皮帶着骨頭完完整整的飛到了老子面前,那張臉咋看咋吓人,我就覺得那是殺雞儆猴,好像他在跟我說你瞧,我死了,你也快了!”
大兵叼着的煙不住的顫抖,他抹了把臉,忿忿說道:“真要我死,老子絕對不眨吧一下眼,可這死的太屈,莫名其妙就挂了,你們說咱四個會碰到啥?”